苏莲托主页
www.suliantuo.net

77、78、79校园文化小说
作者:晓屿
作者授权

内容简介
《冶炼》反映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前三届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。即七七级、七八级、七九级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。以七九级的学生为主。这三届大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,有“老三届”(六六年、六七年、六八年的初、高中毕业生)的学生,有“新三届”(六六年、六七年、六八年的小学毕业生)的学生,有“新三届”之后的下乡知识青年年龄段的学生,有“文革”结束后的高中毕业生,有应届高中毕业生。这几届学生同处一个学校,一个年级,一个班级,彼此性格、年龄差异很大。他们既有共同点,又有不同点。他们互相影响、互为点缀,成为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特殊群体,一个前所未有的、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群体。
小说反映了“文革”结束,改革开放初起这段时间大学的状况,反映了社会的新旧更替对学生的影响。同时,学校的变化、学生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小说在一定层度上揭示了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。
三、温 柔 敦 厚
今天又上了先秦文学课,对上课的李老师,同学们诸多议论。每次大家一提起他,总要议论一番。
记得第一次上先秦文学课,李老师一走进教室,同学们就大吃一惊:他是大学老师?看他那外表,活脱脱一副农民形象:长方型的脸黑黑的,留有明显的农民痕迹。年龄四十岁左右,中等身材。如果不是那整洁的蓝色中山装和那稳实的步伐,简直不能将他和大学教师划等号。即使这样,假如他走在大街上,相信人们也很难将他看着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的。
208寝室的女同学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们心目中的大学教师,议论着现实中看到的大学教师。过去,她们认为大学里的讲师和教授都是那种风度翩翩、气度不凡的学人。进入大学后,看到众多的大学讲师、教授并不全都一个样。这里有温和的学者型,有高雅的绅士型,有平凡的教师型,有慈祥的长者型……而这个先秦文学老师不属于她们心目中的任何一个类型。
一听他讲课,同学们发现了他的特别。他讲起课来严肃、认真、一丝不苟。先秦文学对学生们来说是一门较难学的课程,要对字、词、句进行考究,对大量晦涩的之、乎、者、也文章进行背诵。教师教学时把握不好学生的心理动向,极易使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厌倦情绪。
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,他走上讲台,没多久就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,让同学们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。他讲课没有丝毫的乡土口音,讲课的音调根据课文的内容抑扬顿挫。他对古代文化史、古代历史、古代艺术史相当熟悉。讲课根据需要顺手拈来。对于引经据典的东西能随口背诵出原文并指明出处。他朗读古文、背诵古文的语调非常特别,近似于古书上描写的夫子。在白话文讲授中长大的学生们,被这种中国古典似的教学迷住了。大家发现:古文并不是枯燥无味的。在李老师这里,古文教学非常有趣,韵味无穷,听他讲课,还真是一种享受呢。
还令大家欣赏的是:在课文讲解中,他有时要插入自己的见解。这些见解是不知不觉中出现的,而且时常在把同学们引向他的思维轨道上去后,又来一个急转弯。弄得同学们猝不及防,等到清醒过来以后,不免失笑,从而对他讲的内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今天的先秦文学课,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教材内容涉及到封建统治者对待妇女的态度。此时他大发议论,什么“女人是祸水”,“女人误国”等等,一副对女人不屑和蔑视的态度。见他振振有词地畅说,一些男同学开始附和,教室里有了轻微的嗡嗡声。个别男同学还对着女同学幽默地做作怪象,气得女同学们恨恨地咬牙,心里对老师一百个不满。
谁知正在男同学得意,女同学气恼的时候,他转向了: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,女性一直被压在最底层。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就是男人的统治,大男子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持续了几千年。那些昏君,那些所谓的儒雅之士在治国无道、池破城亡之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,把一切罪过都嫁祸于女子身上。他们不厌其烦地叫嚷:女人是祸水,女人误国。这实际上是统治者推卸责任的借口,玩的是一种卑鄙的伎俩。而由于在阶级社会里,统治阶级的声音总是占据主导地位,这种声音也蒙蔽了不少的黎民百姓。现在是该翻案的时候了。说到这里,他铿锵有力的语言戛然而止。全班同学在短暂的愣神之后,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记到有一次上课在谈到读书问题时,他提到《金瓶梅》,由此又引出一些感慨。他提倡让大学本科学生阅读《金瓶梅》,可《金瓶梅》是禁书。学校里只有教师才有资格阅读,且只能坐在阅览室里阅读,不能借出。他愤愤不平:
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为什么不能阅读《金瓶梅》?不读原著,怎么研究?说是怕学生读了变坏。难道一本书的力量就那么大吗?书有一定的作用,但不能无限制地夸大它的作用。
学生们听他这一说,竟然很合自己的心意,且至今还没有哪个老师甚至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。他们热烈地鼓起了掌……
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李老师的教学。
张小玉突然拿起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上编第一册,翻到某一页,摇头晃脑、绘声绘色地学着李老师的腔调读起书来,大家一听,再一次笑起来,并不时地插进去和她一起学读:
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置彼周行。……

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:“请复卫侯而封曹,臣亦释宋之围,”子犯曰:“子玉无礼哉!君取一,臣取二。不可失矣。”先轸曰:“子与之,定人之谓礼。楚一言而定三国,我一言而亡之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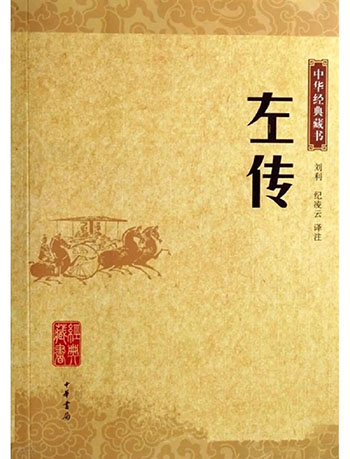
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览揆余初度兮,肇锡余以嘉名:名余曰正则兮,字余曰灵均……吾令羲和弭节兮,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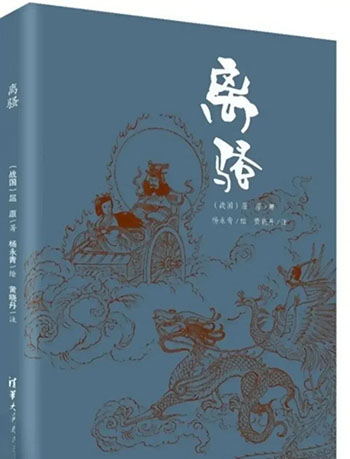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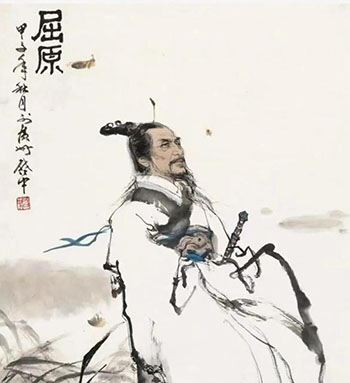
这些篇章分别来自于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离骚》,反正要背,大家嘻嘻哈哈地模仿、作乐,很快就熟悉得差不多能背了。
大家兴致勃勃地一气读了若干篇古诗、古文,都是老师布置的要背诵的篇目。
大家转而又议论起老师来。从他的外貌到他的教学,从他的口音到他的观点,从他的个人到他的家庭,大家喜欢李老师竟然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。大家对他的家庭都不了解,推测他一定有一个贤妻。
张小玉听大家议论起老师的家庭,而大家都不知道。于是她俨然一副万事通,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知道他的情况。”
宋为民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
柯霞说: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?怎么没听你说过?”
“你快说。”龚学山迫不及待地说。
张小玉看看大家,不紧不慢地述说:“她的妻子是农村妇女,现在国家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生活,学校为他的妻子办了农转非并安排了工作。其实你们每天都看到他妻子的,只是不知道罢了。”
大家叫着“谁?谁?”
“就是给我们这栋楼打扫清洁卫生的女清洁工。”张小玉摊出了底牌。
柯霞说:“看来,老师的家境比较困难,他一个人的工资养一家人,师母那点工资微不足道。大学老师还要订书订报,真是太艰难了。”
“从全国来看,知识分子的生活都很拮据。他们刚刚摆脱了‘臭老九’的名声。对于他们来说,这已是最大的安慰。国家承认他们的工作,承认他们的价值,这是最大的快慰。你们看这先秦文学老师,经济那么拮据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。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就是重精神轻物质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。不过在今天,我认为也是一种悲哀。”单云语调铿锵地发着自己的感叹。
宋为民说:“唉,我们也不能帮助他。一来我们是学生没有那个能力,二来也不知老师接不接受。”
“肯定不会接受的,知识分子有一股傲气,同情和施舍的东西绝不会要。”龚学山说。
张小玉接口说:“对,我想最好不要说什么帮助不帮助的话。弄不好,得罪了老师还不知道。”
龚学山说:“学习好就对得起老师了。”
宋为民说:“维护我们这层楼的清洁卫生,减轻师母的工作也是一种报答。”
“中国的知识分子啊,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‘温柔敦厚’”米莉莎想,嘴里竟不自觉地念出来“温柔敦厚”。

孔子
“对,对,李老师不是说吗,孔夫子在政治上提倡‘仁’;在文学方面提倡‘兴、观、群、怨’,提倡‘温柔敦厚诗教说’。传说《诗经》是孔子编订的。老师研究孔夫子,自己都不知不觉地孔夫子气了。嗨,真是。”柯霞微笑着说。
单云待大家议论告一段落后,发表了一通议论:“这个李老师的造诣相当深。他不仅在理论上有研究,就是对古文本身所体现的韵味都研究得入木三分。其实只有这样,才能使古文的教学既体现出它的学术性,又不显得过于严肃、呆板。文言文还是很有价值的。新文化运动时期,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,在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陈独秀、鲁迅为北大教师的同时,也继续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,复辟派人物辜鸿鸣、刘师培为北大教授。这些人腐朽顽固,但在学术上造诣很深。辜鸿鸣精通英、法、德、希腊等多国语言,获得过英国文学博士,对国文和英国文学都有研究。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也相当深。哦,我终于领悟到蔡元培的办学思想的深刻含义了,‘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’。中国的古典式教学方式还是需要有人能够传承下去,应该保留适当的研究领域。”
大家都知道,新文化运动时期,提倡科学和民主。同时提倡新道德、反对旧道德,提倡新文学、反对旧文学,提倡白话文、反对文言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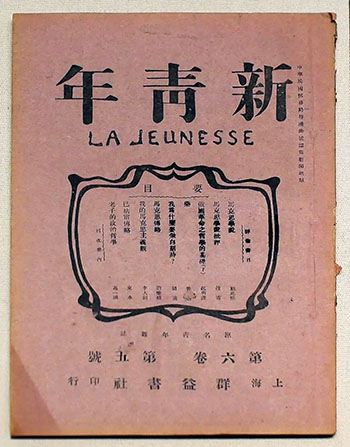
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性刊物
像以往一样,单云说话很少有人插言,尽管他说的不少内容大家都知道。大家对她有一种戒备感。她年龄大,经历相对复杂,平时较严肃,也不怎么搭理同学们,大家对她自然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。加上她一发起议论来就滔滔不绝,大家很难有插嘴的机会。她说完了,大家也不想再说什么了。
米莉莎还在想着刚才讨论的问题。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、考察的蔡元培校长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清晰的比较与分析。在这里蔡元培应该是从两个或者更多个角度思考问题。在当时的中国,显然,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,中国迅速地与世界各强国发生接触、碰撞、冲突及斗争,中国的好些传统的东西无法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,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,是历史的必然。但同时,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沉淀,能够经历数千年而传承下来的东西,必定有着强大的能量和不可评估的价值。所以,蔡元培在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进北大任教的同时,也聘请坚持中国传统文化、有着深厚的传统国学基础和研究的人到北大任教。而当时,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,双方都有不少是留学归国的人,对于有着共同的留学经历的人,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坚持不同的观点、甚至是对立的文化倡导,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停了一会,单云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:“其实我们学校历史悠久,像教我们先秦文学、两汉文学这样的老师有好大一批,有些是民国时期,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名望的人。”
大家一听,心里升起了兴趣。
南方大学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大学,是有民国时期,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名望的人物。
七九级学生还没有到修专修课的时候,所以还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老教授。
但学生们都想见见这些曾经在他们心里神一般存在的老师。
可是不知道怎么去见,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?贸然去见老师,这会打搅老师们,只有等上他们的课时再说吧。
单云说:“七七级、七八级“老三届”的一些同学挨个排出这些老教授,老教师的名单,还逐个上门拜访。”
张小玉接话:“他们这么激动,这么迫不及待地就找老师去了。会不会显得唐突。”
“他们说,要不是“文革”不招生,他们早已上了大学,早就是这些教授们的学子了。”
“哦,这倒是事实。”张小玉道。
米莉莎想:单云是“老三届”的初中生,“老三届”的高三学生,文革开始时,想参加高考的同学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,就等着考试了。结果来势迅猛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使他们没能参加高考,自己投身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了。高考梦延迟了十年,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才有机会进入大学。
“老三届”的学生迫切的求学精神,迫切地渴望亲耳聆听这些老教授们的教诲的心情,可以理解。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初起,这些曾经关注大学的学生,知道大学里的知名人物。
单云说,“当他们按名单寻找老教授时,其中一个人品和学识都让他们敬仰的老教授,竟然在1978年年初,他们进校前在老家病逝了。而这种病逝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是可以避免的。”
顿了一下,她又说:“知道这事后,他们竟然有一种捶胸顿足的痛,有一种捶胸顿足的遗憾。唉,其实,我也有这种感受。”
宋为民忍不住了:“这事在我们这些小同学看来也痛心的。太遗憾了。我们也想见见他呢。是的,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季入校,七八级学生七八年秋季入校。老教授七八年初去世,真是太遗憾了。”
“这老教授无疑是“文革”中的受害者,是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。”龚学山说。
“就是,在“文革”批斗中,他被摔断了一条腿,成了瘸子。但他毅力顽强,坚韧。“文革”后期,还关注着需要他帮助的学生,关注着教学工作。在学校,他帮助了好多有困难的人,其中包括学生。他一个人生活了,夫人早去世了。他工资相对较高,自己生活很节俭。说实话,他自身的身体状况及相关状况并不顺畅,他还关注学生,想着学校的教学工作,这种精神,真是让人钦佩。”单云接着说。
米莉莎想:文革”中,学校这批老教授怕是没有一个能够逃过挨批斗的命运,虽然,七七级、七八级的“老三届”学生没有参与批斗这些老教授,但他们曾经的莽撞行为、野蛮行为也够他们反省和痛悔的。但有一点,他们直接参加“文革”有两年多的时间,随即下农村去了。如果老教授在这两年多后的时间平安无事,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。但运动还在继续,后续问题对于老教授们来说并不轻松。
现在,这几批学生通过高考来到了学校,当然对老教授们格外关注。特别是这个名声在外的老教授更为关注,学校里现在都还流传着他的种种事迹,有褒义的,有贬义的。
就是给七九级上课的个别老师都要提到这老教授的某些传闻。
不知道为什么,单云有些反感这种专门针对这个老教授的负面传闻。
她说:“不过,学校里有人专门喜欢传播他的负面传闻,我就觉得不爽。七七级、七八级好些“老三届”学生和我有一样的看法。别人在奋斗的时候,你在干什么?哼!”
“这种观点我倒是赞同。”张小玉说。
“我也赞同。”宋为民说。
“我也赞同。”龚学山说。
“从尊重老教授,尊重他的学术成就来说,我赞同。”柯霞说。
“但有些东西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,就不好说。”柯霞又补充了一句。
毕竟,在新文化运动时期,这个教授在国学方面的某些观点在历史上有争议。
米莉莎部分赞同柯霞的观点,她认为柯霞受报刊和某些书籍的影响较深,似乎书上的结论都是对的。
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,我们现在更应该从当时历史的条件下来分析看待当时的历史事件,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对立的观点,也不是只能在两种观点中二选一。
现在,“老三届”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南方大学,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时,想要向他求学时,结果他不早不迟地在他们进校前去逝了,怎不让人产生捶胸顿足的痛,产生捶胸顿足的的遗憾。
单云是“老三届”的学生,她与七七级、七八届的“老三届”学生有联系,她的消息来源,应该是可信的。
米莉莎也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痛惜。
讨论告一段落,大家各自忙其他的去了。
大学里,除了学习,学校还要组织一些活动,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,也让同学们在活动中得到锻炼。学校早早放出话来,由各系牵头,组织年级、班级开展活动。这开始静下来的时候,208寝室的几个同学中,有人在脑子里开始琢磨学校开始放出的活动话题。
因为这里面有活动积极分子,有年龄偏大的同学。
点击以下链接,可以进入相关页面阅读
《冶炼》(四、普通话比赛)《冶炼》(五、承 受) 《冶炼》 (七、画展)
《冶炼》(九、求索) 《冶炼》(十、匀 泉) 《冶炼》( 十一、竞 选)
《冶炼》(十二、红五月歌咏比赛) 《冶炼》(十三、情谊无价)
《冶炼》(十四、美学课的启迪) 《冶炼》( 十五、女排万岁)
《冶炼》(十八、“冲出亚洲”) 《冶炼》(十九、暑期采风[1]) 《冶炼》(十九、暑期采风[2])
《冶炼》(二十二、提前召开毕业晚会) 《冶炼》(二十三 走向未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