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莲托主页
www.suliantuo.net

少杰/成都
作者授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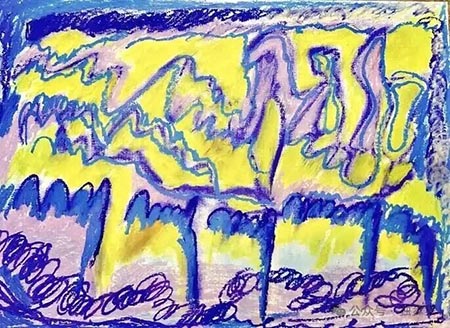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诗词,其音韵声律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律动之河,从上古歌谣的天然节拍启程,经由格律的锤炼而臻于精妙之境,又终在词曲的吟唱中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声律的变迁史,正是中华语言音乐美的不断探索与革新的历程。
声律意识的萌动
先秦时代,诗歌的声韵还处于自然天成的状态。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的动人之处,更多倚赖于句式的回环往复、双声叠韵的天然巧用以及内在的情感力量。如《关雎》中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的叠音,便如流水淙淙,悦耳和谐。然而此时,诗人们尚未自觉地探求四声平仄的规律。
魏晋南北朝,一场深刻的变革悄然发生。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,梵语拼音理论启迪了敏感的文人,汉语自身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四声的奥秘终被明确揭示。周颙著《四声切韵》,沈约撰《四声谱》,如黑暗中的明灯,照亮了诗的世界。沈约更是提出“欲使宫羽相变,低昂互节,若前有浮声,则后须切响”的声律美学理想。此间诞生的“永明体”,正是这种自觉追求的实践结晶。谢朓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中“馀霞散成绮,澄江静如练”一句,平仄错落有致,宛如精工镶嵌的螺钿,标志着古典诗歌步入声韵自觉的新阶段。
格律巅峰的巍峨矗立
唐代诗歌,这座声律艺术的喜马拉雅之峰,其基石由隋代陆法言的《切韵》奠定。此书集前代韵书之大成,成为唐代官定诗韵之祖。唐代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,《唐韵》直至宋代《广韵》,使音韵系统日趋精密完备。
于是,近体诗——律诗与绝句的格律大厦巍然矗立。它要求严格押韵、平仄句式固定、对仗工整。杜甫《登高》中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”一联,平仄安排如精密的榫卯结构,对仗工稳如天平两端,声调抑扬顿挫如层峦叠嶂,完美展现了格律的约束力与艺术表现力的高度统一。此等格律并非桎梏,反而成为诗人表达深沉情感、构建形式之美的精妙框架。王维笔下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之景,也正是在格律的衬托下更显空灵澄澈。
倚声而歌的婉转新声
诗歌的殿堂之外,词以其独特魅力在宋代绽放异彩。词本为“曲子词”,与燕乐水乳交融。词牌即固定曲谱,其句式长短参差,韵脚疏密变化,平仄规则亦较近体诗更为复杂多变。柳永《雨霖铃》中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”的顿挫流转,李清照《声声慢》开篇连用叠字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的哀婉低徊,均体现了词体声律与内在情感的深度契合,其音乐性被推向新的极致。
宋代诗坛亦非沉寂。在成熟格律的重压之下,诗人们开始寻求“拗救”之法以打破常规,于严谨中开辟新境。如黄庭坚诗作常有拗峭之句,苏轼则更注重以气韵行文,有时略破声律而重精神之畅达,如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中“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”之句,便显露出在规则中寻求突破的尝试。
由雅入俗的声韵嬗变
金元之际,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及口语的变迁,词韵系统逐渐与现实口语脱节。词人填词多仍固守《平水韵》,然实际语言中入声已开始消变,词乐的衰微更使词体渐趋案头文学化。周邦彦词中严守四声的“当行本色”虽受推崇,却难掩其与鲜活语言的日渐疏离。
元曲的兴起则带来了声律的又一次解放。曲韵主要依据元代北方实际语音编成的《中原音韵》,其最大特点便是“入派三声”。关汉卿《窦娥冤》中曲词唱白,其声韵更贴近市井语言,自由奔放而充满生机。明清时期,诗坛虽有拟古之风,但戏曲、讲唱文学蓬勃发展,其声韵系统更贴近生活语言,为后世白话新诗声韵探索埋下伏笔。
回望千年声律长河,从《诗经》的自然天籁到永明体的精微探求,从唐诗的格律巅峰到宋词的音乐性升华,再到元曲的市井新声,每一次声律的嬗变,无不交织着语言的精进、音乐的启悟与时代精神的脉动。古典诗词声律的演进,既是中华先民对语言音乐美孜孜以求的明证,亦为后世诗歌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韵律源泉——那穿越千年的平仄回响,至今依然在我们血脉中低吟浅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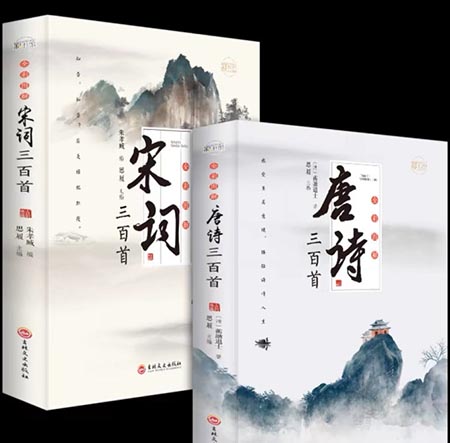
本页图片来自网络,由作者提供
【作者简介】
少杰,本名陈绍杰(陈少杰),出生于1962年6月,四川省大竹县人。198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(现西南大学),《草堂雅集》《草堂雅韵》丛书主编。